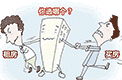贝尔·穆尼(BEL MOONEY)
精神战胜物质的想法总是很吸引人,因为,毕竟我们大多数人愿意相信,也许我们可以改变自己的命运。
作为一名咨询顾问专栏作家,我当然相信这是真的。因此在两半苹果上做实验对我来说似乎是一个放松神经的好办法。
但它确实让我觉得有点愚蠢——每天早上去书房跟一片水果对话。
也许这种感觉是我失败的原因——这让我脱离了真正信仰的过程,因为你一旦开始觉得愚蠢,你就会后退。但我将这一实验继续了下去。
我对标记着“爱”的那半个苹果讲了所有的家人,以及我有多爱他们,因为我无法想出比这更能温暖房间气氛的话题了。我告诉它自己感到多么幸福。
之后我转向了被怨恨的那半个苹果(大约在3米以外)并将精神集中在一对夫妇身上,他们做了件让我难以原谅的事情。我还注入了更多强烈的不满,我头脑中想着无政府主义者,极左派成员,以及伊斯兰狂热分子。这样很容易会散播出真正的怨气。
然而什么都没发生——甚至在建议的两周之后也什么都没发生。哪一半苹果都没有腐烂或有半点变黄。也许我可爱的书房中的气氛充满了爱与和平,以致于我幸运的苹果仿佛来到了一个水果的极乐世界。
萨姆·泰勒(SAM TAYLOR)
和多数同代人一样,我也是60年代的中产阶级父母所实行的“仁慈的疏忽”的产物。就像人们常说的那样,它造就了今天的我。
它教会我坚韧和控制感情的重要。它还教会我没有人会“娇惯”我,我最好还是“忍受”。
因此我认为自己很难对半个苹果表露感情,这是不可避免的。
我一直认为自己是一个有爱的人,并且对积极思想的力量有一种朦胧的信念——尽管这对我的普通中学水平数学考试和瘦腿计划都没什么用。
那么究竟是哪里出错了呢?鉴于在实验结束时可怜的“被爱”苹果的状况,答案是所有的事都错了。我到底失败在哪儿?从那以后我一直这样向自己哭诉。
我跟它说好话。我努力赞扬它,尽管恭维一块被切下来的水果很困难。确实,我没有经常亲吻拥抱它,但我也对它唱了几首披头士的歌。但它仍然变成了一堆灰白色的垃圾果肉。
而被怨恨的苹果似乎却在我的老派养育模式下保持完好。而且我每天对它咆哮一个小时关于水管工的事情,每天早上没化妆对它皱着眉,还有几次摆着手说——我知道,不用报告了。
尽管现在已经置身事外,但我必须要问一个问题:这个疯狂的实验教会了我什么?我不是一个有爱心的人,而是一个无情的独裁者(可能)。或者只是一个疯狂的中年妇女,认为每天跟苹果谈话就可以改变世界而不是吃掉它?
| 上一页 |

 分享到人人
分享到人人 分享到QQ空间
分享到QQ空间










 恭喜你,发表成功!
恭喜你,发表成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