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晓亮:日美同盟关系紧密不意味两国相互利用能够持久
近年来,美国的亚太介入政策无疑是影响日本外交走向最直接、最有力的外部动因。中国作为正在崛起的国家,被日本视为最大“威胁”与“挑战”。日本在“全面正常化”目标与达成目标的资质条件之间尚存差距的情况下,推行了以构建“观念资源与制度资源”为中心的“战略性外交”。
(一)观念资源的构建
观念资源是指政治理念、意识形态、价值观念方面的资源。日本提出的“价值观外交”“积极和平主义”都属于该范畴。“价值观外交”是指日本在对外政策方面重视和加强与所谓具有民主主义、自由、人权、法治及市场经济等基本价值的国家进行合作。
日本提出的价值观外交是一种缺乏“价值”的外交,也是一种实用主义外交,更是一种回避历史反思的既有思维模式的延续。安倍政府之所以热衷于价值观外交,主要背景包括以下三点:从国际格局而言,随着冷战结束与苏联解体,美国视“中国崛起”为新的“挑战”,并制定了“扶日制华”政策,日本则借机奉行“挟美制华”政策。从国内政治而言,日本政界中“革新势力”日渐式微,而急于摆脱“战后体制”束缚的“保守派”势力日益扩张。从国家实力而言,日本在泡沫经济崩溃后陷于长期萧条,与之相对的是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在上述背景下,在日本国内主张“牵制中国”“包围中国”的呼声越发高涨。然而,在价值观外交的衍生背景中并非是为纯粹追求所谓的“普适价值”,其虽标榜“价值”,但实质上却是没有“价值”的价值观外交。
2013年,安倍内阁在倡导价值观外交的同时,又提出了“积极和平主义”。其内阁会议决定的第一份《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和新的《防卫计划大纲》中就明确提出:“日本今后外交安全保障政策的基本理念将确定为以国际协调主义为基础的积极和平主义。”“积极和平主义”的逻辑基础有两个:一是认为日本在战后施行的和平主义缺乏“为了和平而行动的想法”。日本自认为战后做到了不对外侵略、不滥用武力,但是这是消极的和平行为,国际社会期望日本不仅仅不充当和平破坏者,还应积极为世界和平做贡献。二是认为日本缺乏“为了和平而动用武装力量的想法”。日本自认为战后一直对以武力手段维护和平的有效性、正当性抱有抵触心理,所贯彻的是“日本的非军事化越彻底,世界越能够和平”的“消极和平主义”,而这种“专守防卫”的“消极”思想,对“和平”的贡献是有限的、微弱的、局部的,并与日本的经济大国地位很不匹配。可见,从其内在逻辑上看,“积极和平主义”首先表达的是对过去做法的不满,急于修正现有状态。最终将日本变成可以参加“战斗”的“正常国家”。
综上,日本的“价值观外交”明显带有遏制中国的“指向性”,带有追求“全面正常化”的“利己性”,其实质并不是纯粹为了和平、民主和自由,而是以“价值”为手段的工具主义外交;基于国际协调的“积极和平主义”的实质是为了美化其追求“全面正常化”的诉求。
(二)制度资源的构建
制度资源是指对行为体能起到促进或制约作用的体制、制度、政策法规等因素的总和。事实上,日本在外交上积极推进制度资源的构建,其最终目标是为获得更大的“权力资源”,即通过“重塑历史上的强大日本”,进而实现“全面正常化”的诉求。
其一,制度性深化“日美军事同盟”。日美同盟是日本外交战略的基石,日本一直在试图增强外交和安全自主性核心目标之下强化日美同盟关系,因为“失去同美国的同盟关系,可能会成为21世纪日本的噩梦”。日美在安保方面的部长级交流机制除部长级磋商机制外,还有五个局长级别的交流机制,即“日美安全保障高级事务级磋商委员会”、“日美防务合作小委员会”、“日美联合委员会”、“BMD高级运营委员会”和“网络安全对话”。主要是“日美安全保障委员会”(简称“2+2”会议)。2013年10月,该委员会发表了题为《致力于更强大的同盟和分担更大的责任》的共同声明。这份声明被认为有“历史性意义”,标志着“日美两国在近20年来首次实质性扩大军事同盟,将对未来十年同盟关系的发展具有指导意义”。此外,随着日美军事同盟的不断深化,两国加强了在信息共享方面的制度安排。日美信息共享的协商平台主要有:日美安全保障协商委员会、日美安全保障高级事务级协商委员会、日美防务合作小委员会等。在此基础上,为提高美军与自卫队的协同作战能力,两国还共同组建了共享协调指挥机构“日美协同指挥部”,以进一步推进强化军事一体化的进程。
2015年,日美发表了新《日美防卫合作指针》。新指针的主要内容为:(1)美国支持日本自卫队在更大范围内发挥作用,(2)允许日本武装力量在全球扮演更具进攻性的角色,(3)废除了1997年两国防务合作中的地理限制条件,(4)提出了今后日美防务将突出日美同盟关系,(5)建立了从平时到战时所有阶段都能正常运作的“同盟协调机制”和“共同计划制定机制”。可见,“新防卫指针”为“日本自卫队可以出现在世界任何一个角落”提供了制度支撑,至此日本的防务范围呈现出了“本国领土→周边事态→俯瞰全球”的演进图式。
其二,积极构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日本认为自己是“先进的民主国家”,在日美同盟框架下,拥有抵制中国、主导东亚、维护亚太既有秩序的能力。2016年,日本众参两院快速通过了《关于参加TPP谈判的决议》,然而出人意料的是,以“美国优先”为原则的特朗普在其就任总统后宣布退出TPP谈判,至此代表“21世纪贸易规则”的TPP面临难以为继的尴尬困境。对此,安倍一方面试图说服特朗普重新认识TPP的重要性,另一方面积极主导构建“新版TPP”。2016年11月,安倍曾表示:“在美国政权交替之际,为使TPP早日生效需要日本主导推动。”12月,在利马亚太经合组织(APEC)峰会期间,日本推动召开TPP参加国首脑会议。2017年2月,安倍向特朗普鼓吹称:“美国若不主导亚太经贸规制,将会被‘不重视知识产权’和‘以国营企业为主’的中国改写和主导。”在日本主导并积极推进下,2018年3月8日,日本、加拿大等11国在美国缺席的情况下签署了《全面且先进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该协定既有助于减少签署国对中国贸易的依赖,又有利于对中国形成“经济包围网”。
其三,修改《防卫计划大纲》。日本在2010年版的《防卫计划大纲》中强调,未来的作战理念将从“静态的专守防卫”转向“机动的动态防务”,并认为传统的“基础防卫力量构想”已经不适用于现在情况,需要“建设一支能更加有效防止和应对各种事态的动态防卫力量”。2013年1月,安倍内阁对2010年大纲进行了重新修订,并于11月通过了新《防卫计划大纲》。新大纲具有两个重要特点:(1)制定了“坚韧机动防卫力量”和“动态威慑”的构想,(2)深化了日美 “无缝隙军事合作”。此外,还提出,将在2014—2018年间加强日美双边在情报信息、紧急情况、导弹防御、装备技术和日本周边安全等方面的交流和合作。由此可窥见日本提升自身武装力量的步伐。
其四,设置“国家安全保障会议”。2013年2月,日本成立了“关于设立国家安全保障会议的专家会议”,11月通过了《国家安全保障会议设置法》。该法旨在推进由首相官邸主导并制定外交及安保方面的政策,被认为是日本版的国家安全委员会(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NSC)。12月,日本正式成立“国家安全保障会议”。在首次会议上制定了首个《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并用其替代“国防方针”,该战略成为日本“海洋、太空、网络、政府开发援助(ODA)、能源等与国家安全保障相关的各领域的政策指南”。
(三)外交行为中的中国指向性
安倍对中国的态度为什么在短短六年内竟然会从“破冰”豹变为“制衡”?安倍认为,中日邦交正常化时两国确立的“睦邻友好”方针只是实现国家利益的一种手段,手段不能被目的化。由此可见,“破冰之旅”只不过是其对华外交战术上的权宜之计。事实上,安倍从第一次组阁到第二次组阁,其认知结构中始终抱有“夺回强大的日本”的大国情结。而且,在美国的亚太介入政策中,“对日本的定位开始成为根本性问题”。2017年安倍和特朗普在会谈中表示,“如何应对中国是本世纪最大的主题,两国在中国问题上花了很多时间”,“为了促使加强军事力量的中国走向正确的方向,应进一步加强日美同盟”。近年来,安倍内阁已经初步形成了制衡中国崛起的多层架构:(1)炮制“中国威胁论”,处心积虑地“妖魔化”中国;(2)打造“安保三箭”。所谓“安保三箭”,指的是新《防卫计划大纲》、《防卫力量整备计划》和《国家安全保障战略》,意指中国;(3)强化日美同盟,共同牵制中国;(4)拉拢东盟、非洲等,给中国施加压力;(5)推进“价值观外交”和“积极和平主义”,意图边缘化中国。
除此之外,日本在经贸、环境等方面的对华外交行为还继续保持着合作、交流的一面。近年来,虽然中日双边经贸合作处于相对低迷状态,但两国战略互惠格局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而且,日本企业对中国市场的信心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恢复,认为中国市场将继续扩张能够获利,日中经济协会多次组织大量企业家来华访问。2017年5月,自民党干事长二阶俊博表示日中两国有必要加强交流与合作;6月,安倍首次就“一带一路”经济带构想表态:如果条件成熟将进行合作。可见,日本对于中国崛起,在不同时间、不同领域会同时或交替采取“平衡、弱化、稀释、滞阻”与“合作、分享、互惠”等不同取向甚至矛盾的外交行为。
(四)承袭“目的总是证明手段是正确的”的思想
安倍内阁的最终目标是在“夺回强大的日本”中实现“全面正常化”夙愿。然而,日本在实现上述目标的进程中存在三个约束性的枷锁,即日美同盟、和平宪法与战后体制。换言之,日本加速构建“观念资源与制度资源”的过程,亦是其试图“脱日美同盟”“脱和平宪法”“脱战后体制”的过程。而且,日本在上述“三脱”过程中承袭了历史上惯用的“目的总是证明手段是正确的”的思想。
近代以来日本发动的每次对外战争,都是通过向民众蛊惑宣传“为了摆脱西方殖民”、“为了解放亚洲”以及“为了国富民强”等所谓“目的正确”的口号实施的。明治政府诞生后,面临“废除与西方签订的不平等条约”“维护民族独立”“实现近代化”等诸问题的叠加。为了解决上述问题,日本拥有诸多外交行为选择,然而其政治精英却有意识地利用后发国家急于解决内忧外患问题的正当愿望,将国家战略目标与实现路径这两个概念和内涵原本不相同的事物杂糅混淆,用“发展国家”的合理目标去掩盖和粉饰实现手段与行为路径的非正义性和非人道性,用“富国”的目标去证明侵略、殖民与掠夺等残暴手段的正确性和合理性。同样,日本在构建观念资源与制度资源的过程中,也将“目的总是证明手段是正确的”的思想巧妙地嵌入到其外交行为之中。无论是“价值观外交”还是“积极和平主义”,都是证明“手段正确”的最好素材。日本提出“中国威胁论”,也许并不在于中国是否真的是威胁,而在于利用“夺回强大的日本”这一目标证明其宣扬“中国威胁论”策略手段的“正确性”。日本的战略十分明确,就是以“中国威胁论”为借口,在与中国的对抗中实现强军计划。
另外,尽管日美同盟关系愈发紧密,但是这不意味着两国是心心相印、亲密无间的朋友,也不意味着两国的相互利用能够持久。从长时段的历史维度来看,日本加强同盟关系的最终目的绝不是固化同盟关系,而是“脱同盟关系”。吴怀中认为,日本“要让日美同盟为日本国家利益所用、把同盟纳入日本国家战略所需及发展规划中”。近年来,日本不仅将同盟框架作为其实现“全面正常化”的工具装置,而且有试图从“日美同盟下的日本国家战略”逆转为“日本国家战略中的日美同盟”的趋向。
(作者尹晓亮系南开大学世界近现代史研究中心、日本研究院副教授)
摘自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日本学刊》
分享让更多人看到 
- 评论
- 关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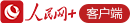




 第一时间为您推送权威资讯
第一时间为您推送权威资讯
 报道全球 传播中国
报道全球 传播中国
 关注人民网,传播正能量
关注人民网,传播正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