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危机的根源:制度、国家建构和世界体系
《当代世界》总第434期刊文《西方危机的根源:制度、国家建构和世界体系》指出,当前西方国家普遍面临严重挑战。西方危机首先表现为根本性的制度危机,但它折射出了西方国家建构模式、西方文化观念和西方主导的世界体系的全面失败风险。
全文如下:
近年来,西方主导的全球化面临失败,美欧国家普遍出现政治危机,自由主义和多元主义的意识形态在西方内部开始遭到批判和抛弃。西方当前的问题是周期性的振荡、演进中的挫折还是根本性的失败?是政治制度的衰朽还是国家建构乃至文明模式的失败?似乎难以给出确定的答案。范勇鹏两年前撰文思考这个问题时,还只是谨慎地将讨论局限在政治制度本身,未敢做出大胆的断言。但随着西方危机的发展和扩散,以及人们反思的深入,现在似乎可以做一较为宏观评估。本文的大体判断是,当前西方危机首先表现为根本性的制度危机,但它折射出了西方国家建构模式、西方文化观念和西方主导的世界体系的全面失败风险。
西方制度的“世袭性”危机
西方制度的根本问题就是不平等的上升和社会流动的停滞。政治归根到底是要解决权力和利益的分配问题。基于人性、权力和利益的分配问题,也就是政治问题,除了使用或威胁使用暴力之外是无解的。无论多么美好的政治,其起源都有着“第一桶血”。人类迄今为止所有的政治制度的本质都是将暴力竞争转化为某种不需要暴力的竞争。在前现代社会,大多数文明都通过血缘继承原则来维护这第一桶血所建立的暂时性分配方案,这大体上与各种贵族宗法制度相匹配,秦以前的中国和近代以前的欧洲都是这种情况。但贵族制度最大的问题是人的血统的不平等以及贵族世系间的永恒战争。如何走出地方性血统政治就成了人类早期文明的普遍追求。
中国较早走出血缘政治的,基于先秦诸子百家塑造的平等观念、春秋战国时期郡县制的产生、秦代开创的统一格局、汉代建构的大一统观念,中国不可逆转地走出了贵族政治时代。这条道路的制度保障就是从举荐到科举逐渐成熟起来的一套选择统治者的方法。通过科举取士这种客观性选拔统治集团成员的方式,本质上就是把需要流血来争夺的权力资源,转化为不需要流血来争夺的知识资源。不管这套制度在后期如何的衰败腐朽,从制度智慧来看,它是前现代人类政治制度的最高峰,保障了中华文明基本的平等性。新中国就是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通过人民和人民的先锋队直接掌权,让人民掌握知识和对人民进行教育等方式,建立了本质上更平等的人民制度。
在走出血统政治方面,其他文明也有不同的尝试,比如中世纪欧洲天主教会和阿拉伯世界的诸帝国都在某种程度上尝试了超越贵族政治、具有一定公共性的制度,部分克服了封建制度的弊端。但是它们均未能建立起完全替代血缘贵族的稳定制度模式,欧洲尤其如此,直到近代初期,仍处在王朝和贵族战争的泥潭中难以自拔。
西方文明基本走出血缘政治,最终靠的是资本主义。“货币是天生的平等派”,解决了千年中世纪未能解决的血统不平等问题,用“财产的不平等代替了基于出身不同的不平等”。这是巨大的历史进步,奠定了西方现代国家崛起的基础。其制度保障就是把需要流血来争夺的权力资源,转化为不需要流血来争夺的财富资源。具体的制度形式始于意大利诸共和国,其特征是商业与金融财富集团掌握政权,以代议制机构进行决策,委托行政首脑进行直接管理。 这套制度经过荷兰的发展,到英国“光荣革命”形成了符合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理想制度,再经过美国的发展和推广,形成了今天西方制度的底色。
与古代中国靠知识来替代权力资源相比,近代西方用财富来替代权力资源的制度有利有弊。利的方面,西方制度有利于增长、创新、活力和科技发展。近代历史上西方国家打败传统中国,主要就是由于这些因素。弊的方面:首先,知识的分配与传播,边际成本较小;与之相比,财富的分配更接近一种零和博弈,容易导致冲突性的政治文化。因而,以知识为权力资源更容易产生权力的扩散和平等的上升,而以财富为权力的资源更容易产生垄断。其次,知识的继承性弱,财富则更易于继承。这就决定了知识的博弈对于每一代人都可以从头开始,而财富的博弈则具有世袭性。第三,知识的获得对健康、智力和人格等有基本的要求,更有利于保障统治者的基本治国能力。财富的获得则有可能完全是由于机会和运气,无法保障基于财富选择的统治者符合基本的要求。这也是为何西方制度一定要采取代议制和责任政府(或独立的行政机关)的原因之一。这些利弊决定了西方制度必然会产生自由急剧扩大、平等严重受限的局面,也就是说,西方现代制度并没有能够完全打破世袭政治,只是有限地突破了封建制,身上仍然烙着中世纪的纹章。
西方制度对人的平等性的提升决定了其在走出中世纪之后能够得到一次大的发展,但上述弊端意味着它给人的平等只提供了非常狭窄的进步空间,历史的发展很快就会撑破西方制度所能承受的上限,19世纪社会主义运动就是对这一上限的挑战。随着平等诉求越发强烈,资本主义制度过渡到社会主义具有历史的必然性,马克思主义已经有充分论述,无须赘言。但是资本主义主动被动地用自己的独特方式阻碍了这一过程的发生:首先,用殖民主义获取额外利润和转嫁危机,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内部矛盾;其次,用民族主义动员社会,通过战争转移了国内冲突;最后,用帝国主义实现资本的全球流动,使资本不再完全受制于国内社会。这些方式都不可能根本解决问题,并且最终导致了世界大战的爆发。但是,世界大战的一个意外后果是摧毁了资本存量和长期积累的经济不平等,而战后恢复期的高速增长又降低了不平等加剧的速度。 于是产生了长达半个多世纪的繁荣、平等和进步的假象。
但是,只要资本主义的逻辑还存在,西方制度就一定会不断复制上述毁灭过程。自苏联解体之后,失去了外部竞争者的西方制度就回到了这个逻辑过程,资本恢复专横、社会急剧分化、贫富差距扩大、权力分配固化,最终使一度生机勃勃的资本主义制度回归到准封建式的世袭制度。因而,今天西方的制度问题绝不是细枝末节的具体困难,而是一个历史性宿命。一些敏锐的思想家观察到了这一问题,比如,皮凯蒂就尖锐地指出了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世袭制”特征,福山虽然不愿意承认,但也不得不讨论美国制度的“再世袭化”风险,杨光斌则直接称美国制度为“封建制”。
西方危机,却不仅仅是西方的,中国虽然有两千年官僚政治传统和近70年社会主义传统,但是市场经济的发展和资本力量的上升,必然会带来同样的问题。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这样一支代表人民性、公共性的力量,或是这支力量没有能够坚持自己的价值理想,那么中国有可能陷入和西方一样的危机。中国模式能否走出不同于西方模式的成功道路,关键就在这里。
共同体建构危机和文化矛盾
正如亨廷顿所说,政治制度只是“文明表面转瞬即逝的权宜手段”,西方的制度危机是比较表面的现象,更深一层的是共同体危机,也就是国家建构危机,以及随之产生的文化矛盾。
前面提到人类文明早期阶段对走出地方性血统政治的普遍需求,这一需求在很大程度上驱动着人类各种政治共同体的发展方向:即从地方性的小共同体走向超地方的统一共同体。统一不仅仅可以带来和平、安全和普遍政治秩序,也可为内部统一市场、大规模社会分工、基础设施建设和高级文化的生产创造条件,现代资本主义还显示了统一带来的技术和产业创新的规模效应。比较中国的秦制、美国宪政和欧洲一体化,如果剥离掉“权利”话语的面纱,其实可以发现它们共享着许多类似目标。因而可以说,统一是人类政治发展首要的“普世价值”。多数古代文明都发生了从城邦时代向统一大帝国时代的过渡,但是统一的程度各不相同,并且除中国之外,其他文明都不同程度地发生了倒退,部分地退回到地方性血缘政治阶段之中。欧洲文明是倒退最严重的,在阿拉伯世界多次形成大帝国之后,欧洲仍然未能走出中世纪。
启蒙运动以来,欧洲才在借鉴学习阿拉伯文化和中国文明辉煌制度成就的基础上,恢复了缓慢的共同体建构过程,与社会相分离的公共性权力在罗马帝国崩溃一千多年之后终于再一次在欧洲大陆上开始生长。今天欧洲各国都是这一过程的产物。以法国的路易十四为典型代表,欧洲终于出现中央集权的民族国家,这在当时是具有巨大进步意义的共同体形式。然而,对于欧洲既是大幸也是不幸的是,共同体建构过程尚未完成,英国就产生了资本主义。自此,资本主义和共同体建构就成了西方文明内部既相辅相成又相互制约的一对逻辑。
按照共同体建构的逻辑,西方应该不断追求在更高层次上实现“一体化”(这也是欧洲基督教政治哲学的理想和各种永久和平论和世界帝国论者的理想),或者说某种版本的“大一统”状态。而按照资本主义的逻辑,资本扩张早期需要国家的护持和重商主义政策,所以会加速政治共同体的形成;但是到资本扩张后期,资本的流动性和国家的地方性之间的矛盾就会突出,资本成为阻碍共同体建构向更高层次发展的因素。
这两种逻辑在现实中碰撞的结果就是,源自英国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通过国家间的竞争和战争迅速在欧洲传播开来,加速了欧洲民族国家建构,同时也导致了民族国家结构的早熟和固化,使之不可能在更高层次上复制共同体建构模式,欧洲由此进入“列强模式”(美国是一个例外,在极特殊的条件下得以初步实现统一共同体的建构)。此后资本跳出民族国家宿主,开始世界性扩张,资本的流动性和国家的地方性之间的张力自此就成了西方文明挥之不去的梦魇。西欧殖民帝国的扩张和宗主国的空心化、东欧传统帝国的崩溃和大量“无根人口”的流散、欧洲列强在世界上的优势地位和相互之间的安全威胁等,这些矛盾本质上都是资本流动性和国家地方性的矛盾所致,最后只有靠战争和革命才能打破这个矛盾。
两次世界大战就是矛盾的总爆发,美国这个特殊力量的存在才使之没有演变成西方文明本身的崩溃。二战后,西方文明和资本主义都获得重生,表面上看迎来了一个黄金时期,但是实际上从来没有真正克服内在的矛盾。共同体建构的逻辑和资本主义的逻辑主要以文化矛盾的方式继续存在,主要体现在以下三种矛盾之中:
一是群体与个人的矛盾。任何共同体的存续,都要以某种集体意识为基础。西方在中世纪主要是靠基督教,近代以来靠共和主义和民族主义。而资本主义要求以个人主义为基础,资本主义的核心价值自由、法治、权利、契约、程序——都是个体本位的。这些核心价值长期以来压制了牺牲、美德、传统等价值观,埋下了国家解体的可能性。
此外,由于来自内部阶级斗争的威胁和外部共产主义的竞争,西方国家不得不吸收了许多社会主义因素,比如普选权、劳动权利、社会保障、妇女权利和少数民族权利等。但是在吸收这些因素的时候,必然要摘除掉社会主义价值中的集体主义本位,将这些权利与个人主义相嫁接。这个过程中就埋下了无法自恰的矛盾:无论是西欧的福利国家还是美国的“新政自由主义”,都是个人主义基础上的赋权运动(entitlement),所以虽然表面上呈现出“进步主义”“伟大社会”或“福利社会”的光环,内部却在酝酿着社会原子化和解体化的风险,加剧了共同体与个人的矛盾。这一矛盾在今天的欧美都已开始爆发,选举制度更将这种矛盾锁死,非革命性变革几无改良的可能。
二是集权与分权的矛盾。共同体建构逻辑必然要求集权,如果没有资本主义的产生,欧洲国家建构会在集权的路径上演进。但是资本要求国家处于一种有限状态,以便于资本收放自如地俘获和控制国家,以及在必要的时候摆脱国家。所以资本主义逻辑导致了个人权利和地方权利对国家权力的制约,这就是所谓“宪政”的本质含义。这两种逻辑之间的冲突不仅使美国、德国等形成了州权制约中央集权的联邦制,而且使已经走上集权之路的欧洲国家也发生了倒退,在二战后大多经历了不同程度的地方分权化过程(近来西班牙地方独立问题仅是暴露出来的少数结果之一),更甚之,在根本上阻碍了欧洲一体化的进展。
三是排斥、归化与多元的矛盾。按照共同体建构逻辑,国家需要促进人口的均质化。有两种可能方法可以达到这一目的:一是排斥,即将异质人口清除出共同体,实现内部的净化(二战前的欧洲主要走的是这条路);二是归化,即将不同的人变成一样的人(二战前的美国主要采取这种方式)。而资本的逻辑主要将人口视作劳动力,不关注其文化属性。例如,在美国历史上,国会多次通过移民法案来缓解国内工人运动的威胁;而在今天的欧洲,面对移民问题,亲资本的力量一直是持欢迎立场的主力。
二战后,美欧各国都进入了一个以赋权为特征的进步时期,平等权利与个人主义的结合(也即部分社会主义价值和资本主义核心价值的结合)产生了“文化多元主义”。自70年代大行其道的各种多元主义是个十分复杂的现象,但总体上符合资本的逻辑而不利于共同体的逻辑。80年代以来,多元主义不断导致西方社会内部的“文化战争”,到今天已经演变成无法弥合的社会分裂。
这三种矛盾合力的结果就是西方文明普遍出现了共同体离散的风险。如果西方文明能够迅速走出这场危机,它也要花相当长的时间重新集聚统一的动能,推动共同体建构的逻辑继续发展。如果西方不能走出这场危机,那么它在未来世界政治中将变得越来越无足轻重。
西方主导的世界体系的失败
人类历史上诸文明的稳定与否,有一个重要的条件就是自足能力。自足能力对文明的地理范围、人口规模、资源能源和生产方式都有一些要求,但是在这些基础上,政治统一的建立是最不可或缺的。中国是人类文明中自足能力最强的,所以也最为稳定(在现代史上,中国也是迄今唯一一个能够不通过向外转嫁矛盾而完成工业化的国家)。西方文明从未长期实现自足状态。资本主义的兴起一方面弥补了西方文明自足能力的短板,使其可以在世界范围内汲取资源,但另一方面也使其在更高层次更大范围上产生了对外部世界的依赖,更加难以自足。因而,不管是单个的西方国家,还是作为整体的现代西方文明,其兴衰都系于其主导的世界体系的成败。从二战后到20世纪90年代,美国逐渐走上了这个世界体系的霸主地位,欧洲日本等第二梯队在美国体系下也享受着部分红利,这是西方现代文明得以生存的必要条件。但现在这一国际体系也出现了解体迹象。
首先,这个体系与美国的国家利益形成了矛盾。70年代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美国通过美元向世界提供流动性来维持美元霸权,但同时产生的长期巨额失衡要靠进口廉价商品来弥补。这个循环有利于美国的短期利益,从长期角度却损害了美国的工业能力和阶级结构。近年来矛盾爆发,这个体系越来越难以为继,美国国内孤立主义和保护主义呼声高涨。
其次,美国主导的体系与英国全球帝国有一个重大区别:英帝国是殖民帝国,对殖民地实施直接统治,虽然本质罪恶,但至少为当地提供了基本的秩序和治理结构,所以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一个有序的体系,甚至英帝国的解体都是在有序情况下发生的;而美国的全球体系是金融帝国,以自由为原则,不关注治理,美国表面上推广民主、法治、人权等,实质上是推广自由原则以服务于本国资本的利益,结果就导致了美国资本所至之处,往往发生自由主义之灾,国家崩坏,秩序无存。随着美国硬实力的衰落,整个体系越发陷入无序状态,反过来损害了美国的利益。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西方文明所建立的所有世界体系,本质上都是剥削性、等级性的,始终面临着其他文明的反抗,不可能稳定长存。
西方主导的世界体系在过去能够稳定存在,既依赖于西方的军事和经济力量,也借助于西方的意识形态。当前西方的硬实力在下降,意识形态力量也在衰落,而且速度有可能更快,这就和现有世界体系形成了一种“正反馈”式的互动:西方控制力的软弱,加剧了当前世界体系的解体;而世界体系的解体,打断了西方国家长期依赖的全球价值链条。
结 论
本文粗略勾勒了西方文明现在所处状态的历史图景。这个图景非常不完备,比如,没有考虑到技术创新有可能发生的巨大作用,没有设想西方通过发动战争来解决问题的可能。但是,在假定其他条件不会发生革命性变化的前提下,我们有理由得出结论:首先,西方的政治制度出了根本性问题,资本失去约束、经济不平等加剧、社会阶级的固化,整个制度发生了世袭化的倒退。其次,制度危机反映了西方国家建构模式和文化矛盾等深层矛盾,它们的根源是共同体逻辑和资本逻辑的矛盾。该矛盾带来了比制度危机更危险的结果——共同体的解体。最后,西方现代文明是一种无法自足的文明,依赖于世界体系而存在。现代世界体系的失败将给西方带来致命一击。
(作者系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副院长 范勇鹏 本文转载自《当代世界》总第434期)
分享让更多人看到 
- 评论
- 关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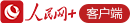




 第一时间为您推送权威资讯
第一时间为您推送权威资讯
 报道全球 传播中国
报道全球 传播中国
 关注人民网,传播正能量
关注人民网,传播正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