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马斯·海贝勒:我亲历的中国改革开放40年
 |
德国的中国问题专家,杜伊斯堡-埃森大学的资深教授托马斯·海贝勒(Thomas Heberer),被称为所有德语国家中最知名的“中国通”。数十年来,海贝勒教授始终致力于在中德两国之间搭建沟通的桥梁。
日前,海贝勒教授接受了人民网的独家专访,从亲历者的角度介绍了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发生的巨大变革。
人民网记者:海贝勒教授,您从事中德交流工作已有50余年时间。最初是什么吸引您对中国产生兴趣呢?
托马斯·海贝勒:在孩提时代,我对地理非常感兴趣。我的母亲经常买地理书给我看。我至今还记得其中一本关于东亚和中国的书。书中讲道:那里生活着世界上最古老、最鲜为人知的民族。我对这个话题非常着迷,探索欲一下子就被激发出来了。年轻的我不禁问自己:不同的名族和文化究竟是如何区分彼此的呢?他们又是如何共存、相互借鉴的呢?
大学期间,我开始学习社会人类学。在确定专业重点时,我选择了中国。1975年,我随旅游团第一次造访中国,非常兴奋。不过还有许多真实的情况我并不了解。我告诉自己:如果要真正了解这个国家和人民,就必须到那里去生活和工作。
回国后我就去了波恩,到中国大使馆询问有没有毕业后去中国工作的机会。1977年大学毕业后,我又去了中国大使馆,正式提出前往中国工作的申请。后来,我在《北京周报》工作了4年半。
人民网记者:您是为数不多的、在改革开放前就对中国有所了解的德国人。您是何时、通过哪种方式意识到中国打开了开放之门呢?
托马斯·海贝勒:原则来讲,中国在我第一次造访的时候仍然是一个非常封闭的国家。外国人根本不可能同中国的老百姓有私人往来。我在《北京周报》的办公室里当时还有3个中国同事,但是他们只能和我谈工作,不允许涉及私人话题。比如我想问问他们孩子上学的情况,却被告知要去找支部书记了解。后来我也就没兴趣再提别的问题了。令人失望的还有专为外国专家提供服务的北京友谊宾馆。因为实行特别管理,任何人没有单位的批准均不得入内。同事来访也必须结伴而行,事后还要接受问询,并做记录。
1978年秋天,情况开始转变。外国专家也有幸看到了邓小平讲话的内容,其中说“98%的外国专家是好的”。此后,进出友谊宾馆的规定也放宽松了。虽然进入宾馆仍需要出示工作证并登记,来访3次以上还要通报所在单位,不过我们终于可以在工作地点之外与中国人交朋友了。
得益于此,我认识了后来的妻子。我们在1979年8月登记结婚,我由此也成为了第一位在文革结束后与中国人通婚的西方国家公民。其实在提出结婚申请的时候,我们都不知道结果会怎样。当时的形式仍充满了不定因素,我甚至有可能被驱逐出境,而我的妻子也可能面临劳改的命运。
人们终于开始感觉到身边的变化。比如《北京周报》的一个女同事烫了一头大波浪来上班,大家一开始还会嘲笑她,后来也就习以为常了。我们可以举办舞会,中国同事们也可以单独进出友谊宾馆,不过最主要的是——食品终于多起来了。当时的中国,一切物资都按计划供应,食品很少,外国人也不例外。比如啤酒的定量是每周3瓶,水果只有苹果。城里市场上销售的也只有很少的几种水果。衣服的颜色只能在蓝、绿、灰3种之间选择。到了1978年,随着经济改革大幕的开启,形势发生了巨大改变。突然之间,居住在北方的人们看到了南方来的水果和蔬菜,肉也多了起来。这是因为农村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民的积极性被调动起来了。
定量分配制度渐渐被取消了。1978年12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进行经济改革,首先是在农村地区推行。我参与了会议文件的翻译和校对工作。我的上司当时到办公室通知我“出趟差”,但并没有说去哪里。我迅速返回宾馆,准备了一周的换洗衣物,然后就同其他国家的几位专家一起被带到了一座封闭的庄园安顿下来。随后我们才被告知,党中央要在这里召开重要会议,决定改革事宜,而我们将负责文件的翻译工作。这是我们第一次听说这个对中国产生了深远影响的会议。
人民网记者:您从10年前就开始呼吁加强中西人文交流。您认为目前这方面交流得到强化了吗?
托马斯·海贝勒:中德人文交流确实加强了。大约从六七年前开始,中国派遣各大院校的博士生前往国外进行为期一年的交流,学习各种理论和方法。中方的态度非常积极,学术交流日益便利化。反之,也有越来越多的德国人前往中国游览、学习汉语、提高汉语水平。交流涵盖了各专业领域的人士,并非只有汉学家。
中德双方都做了许多促进交流的工作。比如杜伊斯堡-埃森大学现有在校生约48000人,其中来自中国的留学生就多达2200人,成为人数最多的留学生群体。除公派生外,还有很多人是自费留学的。这充分展示了双边交流促进工作的成效。
人民网记者:目前的双边交流水平可以算是令人满意吗?
托马斯·海贝勒:这种发展态势的确令人满意。当然,最好的学生不会选择德国,而是前往英语系国家、特别是美国深造。这多少和语言问题有些关系。不过,德国的吸引力也是很大的,尤其是不收学费这一点。在德国的求学成本比起在中国国内一些大学或者其他国家的大学还是低不少的。此外,还有一些学者来到这里——按照他们自己的话来说——“驻扎”一年。因为国内要求他们必须有一年以上的海外经历并提供证明才能参评教授。这项新规表明,人们已经逐渐把海外经历看作科研人员一项不可或缺的素质了。
人民网记者:您在过去的几十年间见证了中国的飞速发展。您对中国的下一个10年又有何期待呢?
托马斯·海贝勒:第一,中国在2013年的时候决定转向全新的发展模式。单纯追求增量的理念将被高质量发展理念取代,可持续性将成为发展的关键。从只求增量到谋划可持续发展,这无疑是一个决定性的转变。
第二,扶贫。这也是中共十九大强调的重大课题。上世纪70年代末,中国生存在贫困线以下的人口估算为3亿。直到前几年,中国的贫困人口仍有4500万左右。如果采用世界银行日均可支配收入不足1.5美元的贫困标准计算,那么中国仍有约五至六千万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也就是说中国仍存在贫困问题,特别是在山区、闭塞地区以及少数民族地区。中国计划在2020年彻底消除贫困。
第三,改善环境。在这方面中国也设定了目标:到2035年彻底改善环境状况。这也是非常重要的工作。
第四,工业升级。中国的目标是在先进技术领域,如机器人、数字化、人工智能、电动汽车等,占有世界领先地位。
第五,也是我的一点希望,那就是中国能够加强与国际标准的对接。
人民网记者:作为中国问题专家,您经常受邀担任中国政治、经济问题的顾问,或者随代表团访华。您还曾于2016年陪同德国总统高克访问中国。您在这些访问活动中的主要任务是什么?
托马斯·海贝勒:我认为顾问是一项重要的工作。当然,政治家的职位越高,为他提供顾问服务的难度也就越大。比如给市长当顾问和给联邦总统当顾问就不能同日而语。
原则来说,我的任务就是帮助政治家更好地理解中国,特别是中国的多样性。中国呈现出的并不是单一的景象,能够让人做出一般性的总结和判断。恰恰相反,中国各省区市乃至各县的情况都不尽相同。德国的政治家应当努力去理解中国制度的内在逻辑和运行模式,否则很容易得出错误的结论。我认为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对于接触较少的人来说,中国的体制和机构非常难于理解——原因就在于多样性 以及特殊的政治、文化历史。因此,我们需要翻译人员把各种关于体制、机构、职能和运行模式的信息翻译过来。
我想,所有的社会原则上来说都会面临类似的问题,但解决问题的方式却不尽相同。我们头脑里必须时刻有这个意识。这是全球社会如今共同面临的问题。我们可以多思考一下全球化带来的环境问题、技术研发、数字化、就业问题等等。为政治家阐述这些问题,在我看来是一项重要的工作。
人民网记者:最后再提一个私人问题。您从事了这么多年的中国研究工作,最令您感到骄傲的事情是什么?
托马斯·海贝勒:“骄傲”这个词可能不太合适。骄傲是建立在自我功绩上的。而我之所以能够在这样的宽度、广度和多样性程度上从事中国研究,与中方的支持是分不开的。研究工作需要合作伙伴,而不是直接跑到中国去询问、研究。我在长期工作中与合作伙伴建立了互信。多年来,我一直邀请一些机构的人员来德访问,同时也派遣德国青年学者赴华。这样一来一往,就建立起了信任,联合科研工作也变得方便多了。我觉得这一点非常重要。
还有一些事情,虽谈不上骄傲,但同样非常重要。2002年,我募集了20万马克善款,用于在四川省彝族地区捐建学校。这可以说是令我略感骄傲的事情。我还经常回到那里走一走,看看之前失学的孩子们是不是回到了校园。我认为对于学者来说,做这样的事情和科研工作一样重要。我们应当设身处地地为接受我们调研的人着想,并尽可能地为改善他们的生活条件贡献微薄之力。
2008年奥运会期间,一些媒体抹黑中国形象。我在德国《日报》发表了题为《反对妖魔化中国的14个论点》的文章,反响强烈,引发了读者广泛讨论。这样的工作也能够发挥沟通桥梁的作用,是我一直希望做的事。
点击阅读德文版:
http://german.people.com.cn/n3/2018/0705/c209050-9477998.html
分享让更多人看到 
- 评论
- 关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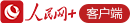




 第一时间为您推送权威资讯
第一时间为您推送权威资讯
 报道全球 传播中国
报道全球 传播中国
 关注人民网,传播正能量
关注人民网,传播正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