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澎:日本的战争记忆是如何选择和建构的
 |
|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日本社会研究室主任胡澎(林昶 摄) |
人民网8月18日电 由中国日本史学会和北华大学联合主办、北华大学东亚历史与文献研究中心承办的中国日本史学会2016年年会暨“日本的社会变迁与中国”学术研讨会12日在吉林省吉林市举行。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日本社会研究室主任胡澎表示,日本总是片面强调受害,回避加害责任,这与日本作为侵略战争的发动者和加害者的历史事实相违背,也与战争受害国民众的战争记忆产生较大错位,导致历史认识问题成为中日关系中的一大障碍。
胡澎在发言中指出,因战争亲历者相继离世,大多数日本人所记忆的战争已与史实有了相当大的距离,研究日本人的战争记忆问题以及思考中、韩、日等国如何重构和共享接近历史事实的共同战争记忆,不但重要而且具有现实意义。
片面的受害者记忆
胡澎认为,当今,大多数日本人的战争记忆是片面、扭曲和中断的,呈现出强烈的受害意识。
战时物质生活的窘困、家庭破碎、亲人离散、东京大空袭、广岛和长崎的原子弹爆炸等,构成了日本人对战争的主流记忆。日本人牢记着两个与战争有关的日子:一个是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纪念日,另一个是8月6日广岛原子弹爆炸纪念日。8月15日在日本通常被称为“终战日”,这一表述回避了“战败日”、“无条件投降日”的字眼,同时也回避了那场战争承载的罪恶和教训。日本学者藤原彰认为,8月15日作为战争的纪念日,是从被害者的立场上倾诉国民的感情。于是这一天就被称为“终战纪念日”,意思就是说,由于天皇的“圣断”才结束战争取得了和平。所以日本人根本没有意识到战争是对亚洲各国的侵略性的战争,没有认识到日本对朝鲜和亚洲许多国家来说是加害者。每年的8月6日,广岛和平纪念公园都会举行隆重的纪念活动,悼念原子弹爆炸中的无辜牺牲者,日本各大新闻媒体连篇累牍地报道广岛的“受害”,构成一个战争“受害者”的想像的共同体。这一天,很少有人去深究战争是谁发动的?日本军人在海外战场都做了些什么?为何日本会遭到原子弹爆炸?如同“安息吧!过去的错误将不再重复!”这句刻在广岛原子弹爆炸受害者纪念碑上的碑文,主语是谁?谁犯的错误? 为什么会“被爆”?均被故意隐去了。
战后,日本出现了大量描绘战争的残酷以及给日本人身心造成巨大伤害的文学和艺术作品,甚至出现了在世界文学中独树一帜的“原爆文学”。日本的历史博物馆中,几乎没有揭露侵略战争和殖民统治等加害行为的展示,一味突出日本民众的战争受害状况。西方一些学者曾尖锐地指出日本人片面的战争受害者记忆。英国学者布衣曾批评道:“对大多数日本人来说,广岛是太平洋战争巨大的象征符号,日本人所有的苦难,都能浓缩到这个近乎神圣的字眼‘广岛’里面。除了民族与国家的殉难这一象征意义外,广岛也是绝对罪恶的符号,常常被人们拿来与奥斯维辛相提并论。”德国学者沃尔夫冈?施文特克也阐述道:“北京郊外的卢沟桥事变或者珍珠港事件在日本人的战争记忆中并未占据显著位置,反倒是冲绳、广岛和长崎留下了深刻印象。简而言之,在日本,受害者的角色比罪犯的认知要强大得多。”
由于记忆具有主观性和身体性的特征,因此,作为个体的日本人对战争年代遭遇的苦难以及丧亲之痛有着深刻而痛苦的记忆,这本无可厚非。然而,当个体身体体验的战争受害记忆上升为日本人的集体记忆乃至民族记忆,一味沉浸在本民族的受害情绪中,甚至以战争受害者自居,对被侵略国家民众的伤痛和感情缺少体察,甚至漠视、轻视、无视,则是错误和危险的。
综上所述,当日本人的战争“受害意识”被固定化以后,面对中韩两国对日本正视历史、反省和道歉的要求,对劳工和“慰安妇”予以道歉和赔偿等要求,有相当数量的包括政治家、知识分子和民众在内的日本人难免反感和抵触心理。其意识深处潜藏着这样的逻辑:作为战争受害方的日本为什么要对战争反省、忏悔和道歉?
被建构的受害者记忆
胡澎分析称,“记忆并非一个不变的容器,用来盛装现在之前的过去,记忆是一个过程,而不是一件事物,在不同的时间点上它的工作完全不一样。”如何建构战争记忆是一个尖锐、敏感的话题,同时关涉到权力的作用、社会变迁、文化导向,以及遮蔽战争加害者的主观愿望等。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作为战争加害者的记忆被抹消或选择性地忘却,大多数日本已习惯置身于受害者的立场去记忆战争,缺少从加害者的角度去反思战争,思考战争责任,这与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日本民族保守主义思潮的大行其道有关,同时,也受到历史修正主义的影响。日本政要多次参拜靖国神社,一些民族保守主义政治家、历史修正主义者、右派媒体人一直抵制对那场侵略战争的否定性评价,不断抛出否认南京大屠杀言论,对强制劳工、三光作战、从军“慰安妇”、七三一细菌部队、日军遗留生化武器等战争遗留问题否认、抹杀或故意缩小。凡是客观反映日军加害行为的叙述均被扣上所谓“自虐史观”、“反日史观”的帽子加以攻击。针对这一系列历史修正主义的动向,山田朗曾一针见血地指出:“慰安所和慰安妇的相关话题,已经是铁的事实,但对历史修正主义者来说,却认为这是有损日本人荣耀的事,将是否存在强征的问题矮小化,将问题的存在本身也试图隐藏起来。”由此可见,权力在日本人战争记忆的建构中发挥着不可估量的作用。德国学者沃尔夫冈?施文特克也曾指出“自民党的政治领袖、文化领域的官僚和国家媒体的一部分在当前组成了一个意见垄断集团,他们出于政治的目的把历史加以工具化利用。”
靖国神社内设的游就馆中的解说词和展板所代表的是所谓“靖国史观”,它将侵略战争的爆发归咎为美、英的“挑衅”和“压迫”,将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目的粉饰为帮助亚洲摆脱白人殖民统治,实现“大东亚共荣圈”,标榜和宣扬日本军人“战功”和为天皇尽忠效死的“武士道”精神,否定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审判,将被处死的甲级战犯视为受战胜国迫害的殉难者……
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出现了一批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自由主义史观研究会等右派保守组织,还有藤冈信胜、西尾干二等一批右翼学者。他们编辑出版了多部宣扬、美化、掩饰日本侵略战争的书籍,如《大东亚战争的总结》对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性质进行全面的翻案,强调那场战争是日本把亚洲从欧美的统治下“解放”出来的战争,为侵略战争寻找冠冕堂皇的理由。该书否认战争中日本军队对亚洲各国人民造成的痛苦与灾难,声称南京大屠杀是“虚构”,“从军慰安妇”是商业性质,呼吁建立日本人自己的历史观。《“自虐史观”的病理》、《教科书没有讲授的历史》、《污蔑的近现代史》、《国民的历史》等书籍也都是在宣扬这一类观点的。
一个民族的历史是通过历史教科书建构、记忆和传承的。2001年,文部科学省审查通过了右翼团体“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主导编写、扶桑社出版的初中历史教科书。该教科书蔑视亚洲、将统治韩国殖民地正当化,主张南京大屠杀和“慰安妇”等历史事实都是伪造的,对日本侵略战争进行肯定和美化。子安宣邦认为在历史教科书中将“侵略”战争改写为权益防卫的不得已的军事“进攻”,这种国家对教科书检定的行为是国家一方发动的对过去记忆的“变换形式的再生”,是要谋求对过去的“重提与再叙述”。
安倍当局深知重塑民族历史记忆的重要性。2015年是日本战败70周年,早在年初,安倍晋三就设立了专门委员会为起草战后70周年谈话做准备。8月14日,“安倍谈话”发表,虽然迫于日本国内和国际社会要求日本正视历史的呼声,“谈话”中使用了“侵略”、“殖民统治”、“反省”、“道歉”等字眼,但模棱两可、遮遮掩掩、闪烁其词的态度令战争受害国的民众感到缺乏诚意。“安倍谈话”发表当天,日本外务省就从其官网上删除了刊有“村山谈话”等前任政府对战争“深刻反省”、“由衷道歉”内容的网页。
日本的民族保守主义政治家、历史修正主义者、右派媒体人妄图通过淡化和模糊战争责任,将战争定格于原子弹爆炸,混淆战争的加害与受害的关系,将受害作为日本人和其他战争受害国人民共同拥有的经历。在他们眼里,供奉着二战战犯灵位的靖国神社既是体现日本近代以来为国家“牺牲”的人们的人生价值的场所,也是消解丧失亲人的痛苦记忆的装置。小泉纯一郎首相在参拜靖国神社时说道“战死者们崇高的牺牲才有我们今天的日本”,这句话令我们质疑他是要以“国家荣誉”和“牺牲”来取代日本人作为战争加害方的负罪感。高桥哲哉在《国家与牺牲》一书中针对小泉的说辞予以揭露:“通过颂扬战殁士兵‘崇高的牺牲’,把这种牺牲作为‘敬意和感谢’的对象予以美化,会产生某种重要的效果,那就是会产生一种掩盖、抹消亚洲太平洋战争的惨状、在战场上阵亡的惨死和不快的效果。”
个体记忆与集体记忆之间存在着共谋关系,在既是受害者也是施害者这样一组辨证的关系中,大多数日本人选择了“历史失忆”,这既是一种选择性遗忘,也是一种作为加害者自我保护性的遗忘。因此,我们经常看到,很少有日本人提起战争中对他国的侵略行径、大屠杀、惨案,似乎战争仅仅意味着广岛和长崎的“被爆”、日军战俘在西伯利亚的惨痛经历。这种选择性记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作为战争加害方企图逃避和推卸战争责任的一种主观愿望。学者藤原归一曾指出“日本国民并非是因为经历了太长时间而遗忘了战争,而是因为不愿看到某种东西而早早的闭上了眼睛”。在战争历史真相面前,选择性记忆和遗忘的目的其实就是要剥离自己与罪恶的关系。
在日本政治权力的操控以及错误历史观念的影响和推动下,日本从侵略战争的“发动者”、“加害者”同时也是战争“受害者”的身份置换成了战争“受害者”。在巧妙的概念偷换以及有选择性记忆的建构之下,越来越多的日本民众遗忘了日本是战争的“发动者”、“加害者”、“参与者”,习惯于将日本定格于“受害者”的立场。作为战争“加害者”的立场和记忆的遗忘与缺失,以及对战争“受害者”意识和记忆的强调和传承,其后果是严重的,与中、韩等被侵略国家的民众的战争记忆发生了严重的背离。
民间力量客观记忆的努力
胡澎强调,二战结束至今,针对否认侵略战争历史史实和否认侵略战争性质的逆流,一些爱好和平的日本人和日本民间组织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他们不但作为战争的受害者来反思战争,同时也站在加害者的立场,思考和研究日本的战争责任。在对抗日本右翼团体和右翼政治家的错误历史言论,捍卫历史真实和客观记忆战争等方面做出了积极努力。
这些民间团体数量众多,有以反对化学、细菌、核武器为己任的“日本ABC企划委员会”、支持日军细菌战受害者索赔的“要求国家赔偿七三一部队细菌战受害者诉讼律师团”、“七三一细菌战审判运动委员会”、针对否认南京大屠杀舆论成立的“南京事件调查研究会”、“调查南京大屠杀全国联络会”、“南京证言会”以及支援中国战时被抢掳劳工、要求日本国家赔偿的“日中劳动者交流会”、“支持中国人战争受害者要求会”等等。有些团体规模不大,但深入日军侵略过的国家采访战争的受害者、幸存者,亲手调查、搜集战争期间日本军队的罪行和证据。有的团体顶着右翼势力的压力,克服经费紧张等困难,编辑有关侵略战争的资料集、发行简报、举办演讲会、展示会。
为了阻止各地教育委员会采用扶桑版右翼教科书,一些民间团体分别在2001年和2005年发起了两轮“让扶桑版教科书采用率为零”的运动。“日本律师联合会”中一些具有正义感和良知的律师不但关注中、韩等亚洲各国对日民间索赔运动,还从法律、道义、人力和资金等方面提供了支持。
著名历史学家家永三郎在其编写的《新日本史》教科书中记载了日本在二战中所犯罪行。为抗议文部省的删改,与之打了长达35年的官司。《朝日新闻》记者本多胜一是第一个站出来,全面采访、揭露日军侵华罪行的日本记者,也是第一个将整个南京大屠杀的历史告诉日本人民的学者,《南京大屠杀始末采访录》等多部关于南京大屠杀历史研究的书籍让日本读者了解到这段尘封的加害历史。小学教师松冈环20多年来致力于南京大屠杀的民间调查,在日本先后寻访了250 多名二战老兵,并自费80多次到中国访问,与300多位大屠杀幸存者会面。她自编自导的纪实电影《南京,被割裂的记忆》以7名日本老兵和6名中国幸存者的真实故事为主线,从中日双方的视角再现了那场可怕的灾难。学者野田正彰在他的《战争与罪责》一书中对八名原侵华日本军人进行了采访,通过他们在战犯管理所的改造,细致入微地刻画了他们人性的回归过程,对他们的战争记忆进行了挖掘和剖析。津田道夫的《南京大屠杀和日本人的精神构造》揭示了战前日本每个国民都直接或间接的成为日本向外扩张发动侵略战争中的一员,提出日本国民有责任对当初支持战争进行反思。
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出版了一批反映被侵略国家民众的苦难的调查和研究类书籍。如:石田米子、内田知行编著的《黄土地村落里的性暴力——大娘们的战争仍未结束》、上田信的《鼠疫与村落——731 部队的细菌战与受害者的创伤》、关成和的《被731 部队占领的村落——平房村的社会史》、石井弓的《作为记忆的日中战争》等。他们“将个人的受害记忆作为学术研究的对象,从遭受战争摧残的个人及地域社会的角度分析战争的破坏机制和造成的后果,自下而上、自微观而宏观地解读历史。” 这些有良知的日本学者、知识分子、普通民众既有战争受害者的意识,同时又具备战争加害责任的自觉,是针对日本人片面选择受害者记忆而做的努力。
分享让更多人看到 
- 评论
- 关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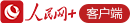




 第一时间为您推送权威资讯
第一时间为您推送权威资讯
 报道全球 传播中国
报道全球 传播中国
 关注人民网,传播正能量
关注人民网,传播正能量